 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
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  不良信息舉報電話:陜工網(029-87344649)
不良信息舉報電話:陜工網(029-87344649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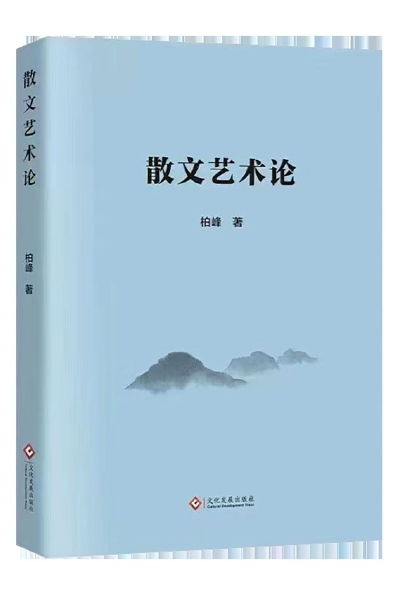
柏峰寄來三本著作:《散文藝術論》《千山萬壑走洛河》與《行走黃河太華間》,說是讓我“批評指正”。柏峰是著名的文化學者、散文藝術專家,“批評指正”顯然是客氣話,其實是讓我夸他幾句,老朋友了,我欣賞,我情愿。
認識柏峰很早。女兒閻荷在《文藝報》編副刊時,同柏峰有過交往,記得是商討有關校注寫法別具一格的古典長篇小說《何典》的一些問題。
閻荷告我說,柏峰老師是做學問的,滿腹經綸。我說,柏峰老師多年來一直埋頭做學問,他校注《何典》,一般人連《何典》看都看不懂。
閻荷去世,我想念她,無以寄托,散文來叩門。我學寫散文《我吻女兒的前額》,頭一句話是“美麗的夭亡,她不相信眼淚”。我寫人道主義者黃秋耘的題目卻是《黃秋耘相信眼淚》。在《黃秋耘相信眼淚》之后,附有王蒙來信。
2002年3月底的一天,王蒙秘書到處找我,說有急事,要我回電話。翌日,我撥通王蒙的電話。
我問:聽說你找我?
王蒙:你的電話變了?我看了《文藝報》上你寫黃秋耘的文章,挺好,打動了我,令人嘆息。你的文字老辣,你老成精了,不但辣,甚至毒!我感謝你。
我說:你和黃秋耘交情深。
王蒙:我也寫過一篇黃秋耘的,發在《新文學史料》上。
我說:你那篇文章才叫好呢!
王蒙:我說閻綱,咱倆不要互相吹捧了,我那篇淺薄多了。你并非一味地褒,而是褒中有貶。接著寫,這年頭,什么不能寫?你的文章漂亮得不得了。你現在的電話?
我說:67600008
王蒙:4個0、1個8?好啊!我4月1日出國,所以急著找你。以后咱們多聊。
王蒙之所以急不可待地同我通話,我想并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如何如何,而是文章觸動了他那根最敏感的神經,勾起他對于故去的黃秋耘從《文藝學習》批判《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》以來“愛我友我”的無限懷戀。對于他們二人竊竊私語、終成友誼的幾段接觸,我是記得的。
王蒙即將去新疆時,兩人在什剎海游泳,不期而遇,王蒙戲稱:“涸轍之鮒,相濡以沫,未若相忘于江湖。”從茲惜別,一個天南,一個地北。
王蒙當部長以后,身份的改變讓他感到不小的壓力,萬分苦惱,他倍加小心。他借出差廣州之便,專程拜望黃秋耘。黃秋耘未忘于江湖,當面贈言諍諫:“寄語位尊者,臨危莫愛身。”王蒙深受感動。所以,當他看到我寫黃秋耘便勾起重重心事:從人生起伏波瀾,到最后如期掛冠,百感交集,江海翻波浪。
《我吻女兒的前額》發表后,很短時間38家報刊轉載。《黃秋耘相信眼淚》以及王蒙的讀后感傳遍文壇。其后,我撰寫了長篇散文《美麗的夭亡——女兒病中的日日夜夜》,并且進行散文理論的研究,讀林賢治和王兆勝,讀《金薔薇》,讀《歌德隨想錄》,還寫些自己的體驗和心得,什么寫散文:純情——傳神——帶體溫;什么“為規范寫作,給自己立下十條規矩”。但這一切,細讀柏峰今年3月剛剛出版墨香可聞的《散文藝術論》之后,我大為驚喜,臉上發燒,特別推崇。
《散文藝術論》寫自“無韻之離騷”的《史記》兩千多年以來“散文的發展史”,以及對現當代一大批大約百名作家的作品列章予以分述,探索“散文的藝術”,文筆簡潔,富有哲理。
他在按不同時期條分縷析百名作家的作品之后,再按不同時期總結如下(為了簡練,僅選取其核心價值判斷片段言詞)——
一、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散文吸收古典散文的精華,晶瑩的露珠,熠熠發光。大量的留學生(魯迅、胡適、徐志摩等)學成回國,帶進異國新思潮。
二、現代女性的散文在叛逆的道路上更義無反顧,一些男性作家望塵莫及。
三、新中國成立后的前17年的散文,塑造了各條戰線涌現的新人形象。
四、改革開放時期的散文風格各異,燦爛輝煌。
試想,這是多大的工程啊!篳路藍縷,斬棘前行,艱難困苦,研究考證,花費了多大的精力,頭發掉了幾根根,透支寶貴的生命,誰解其中味?
這是迄今較為全面完整的散文藝術論集,真誠可貴,我特別推崇,故而,向柏峰表示祝賀并向文友們廣而告之。□閻綱
責任編輯:白子璐

關注公眾號,隨時閱讀陜西工人報